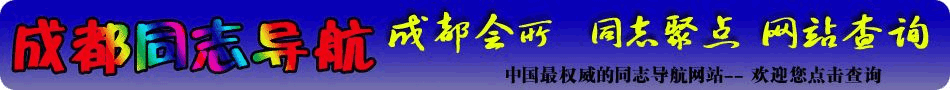|
窗台的外面摆着一小盆野菊,开花的时候,嫩黄嫩黄的几朵,犹如阳光残留下的余印,羞涩地垂在枝叶的身上。 偌大的一个窗台,只这孤孤单单的一盆,放在正中央的窗前。 一盆野菊。 他妻子不喜欢这满山可见的植物,多次拉着他的手怪道: “别人还以为我们恁没情趣,种起这些野草野花来了!瞧它,你换点其他的种吧,在窗台上多种几盆。” 他总是哄她,告诉妻子自已喜欢。 一次,妻子买了一株开着淡紫色的兰花。一进门,就是一阵的极为淡雅泌人的芳香。 “好看吧?!我托朋友买的,名贵着呢!” “嗯!”他淡淡地一笑,“摆客厅里,有一盆这样的花让人看着好舒服,何况又这样香。” “我是买来让你放在窗台上的,”妻子不解地说道,“那盆也太不成样了!” “不用了,这花看起来都挺难伺候的,放窗台谁能养好它,死了怪可惜的!”说完,转身进了屋子,留下一脸兴奋捧着花呆呆站着的妻子。 花了几天时间,总算安抚下妻子,那盘兰花被送给了隔壁家的一个老阿姨,对方接过谢个不停,妻子一脸郁郁,他又赔着笑脸逗了好久,才让妻子忘记。 他喜欢野菊,也许是因为那个种菊的花盆。那个有些不规则的盆上,有两个大拇指的指印,一个是自已的,另一个不是他妻子的。 是他的。 他也曾笑过他喜欢野菊这个古怪的爱好。他问为什么喜欢,他没说。 很多东西喜欢上了,很自然的,根本说不上理由。 那次不知为什么吵架,一直好几个月没见面。他不安得一直打电话,赔着小心。那时菊花正开,他专门跑到郊外,摘了一大束的野菊。 黄黄的,一小朵一小朵的,象缀在土地中的暖阳。 他花了些时间,学做了个陶盆,让他印了一个指印,自已也印上了一个。 “种株野菊在这里面吧!我们两人的,一起呵护它,还可以天天牵着手,勾着手指头,而且……”他装怪地顿了顿,用带着笑的眼睛看他,“你就是一株野菊,我就是这盆!!” 他一脚蹿去,笑着骂他令人做呕!真还以为是人鬼情未了,老套的招式。 第二天,他窗台上所有的花都孝敬到了父母的窗前,只摆上一盆野菊。 他轻轻用手指敲着盆沿,像是敲着他的脑门,一般地清脆。 仿佛昨天。
偌大的一个窗台,只这孤孤单单的一盆,放在正中央的窗前。
一盆野菊。
他妻子不喜欢这满山可见的植物,多次拉着他的手怪道:
“别人还以为我们恁没情趣,种起这些野草野花来了!瞧它,你换点其他的种吧,在窗台上多种几盆。”
他总是哄她,告诉妻子自已喜欢。
一次,妻子买了一株开着淡紫色的兰花。一进门,就是一阵的极为淡雅泌人的芳香。
“好看吧?!我托朋友买的,名贵着呢!”
“嗯!”他淡淡地一笑,“摆客厅里,有一盆这样的花让人看着好舒服,何况又这样香。”
“我是买来让你放在窗台上的,”妻子不解地说道,“那盆也太不成样了!”
“不用了,这花看起来都挺难伺候的,放窗台谁能养好它,死了怪可惜的!”说完,转身进了屋子,留下一脸兴奋捧着花呆呆站着的妻子。
花了几天时间,总算安抚下妻子,那盘兰花被送给了隔壁家的一个老阿姨,对方接过谢个不停,妻子一脸郁郁,他又赔着笑脸逗了好久,才让妻子忘记。
他喜欢野菊,也许是因为那个种菊的花盆。那个有些不规则的盆上,有两个大拇指的指印,一个是自已的,另一个不是他妻子的。
是他的。
他也曾笑过他喜欢野菊这个古怪的爱好。他问为什么喜欢,他没说。
很多东西喜欢上了,很自然的,根本说不上理由。
那次不知为什么吵架,一直好几个月没见面。他不安得一直打电话,赔着小心。那时菊花正开,他专门跑到郊外,摘了一大束的野菊。
黄黄的,一小朵一小朵的,象缀在土地中的暖阳。
他花了些时间,学做了个陶盆,让他印了一个指印,自已也印上了一个。
“种株野菊在这里面吧!我们两人的,一起呵护它,还可以天天牵着手,勾着手指头,而且……”他装怪地顿了顿,用带着笑的眼睛看他,“你就是一株野菊,我就是这盆!!”
他一脚蹿去,笑着骂他令人做呕!真还以为是人鬼情未了,老套的招式。
第二天,他窗台上所有的花都孝敬到了父母的窗前,只摆上一盆野菊。
他轻轻用手指敲着盆沿,像是敲着他的脑门,一般地清脆。
仿佛昨天。福建同志,福建男海,泉州男海,厦门同志,泉州同志,福州会所,厦门男海,泉州男孩,福建同志交友
|